原创 胡雪岩频繁娶妾,常常一夜过后就休掉,学者:难怪胡雪岩能成首富
数百两白银的"演出成本"
账房先生翻开账本,又记下一笔开支:遣散费,白银三百两。
这已经是本月第二笔了。
胡雪岩的娶妾频率,让整个杭州城的茶馆都有了谈资。

媒婆刚把新人送进门,不出三日,管家就会备好银两,客客气气地送人离开。
新娘子哭哭啼啼,街坊邻居窃窃私语,胡家的名声就这样传遍了整个江南。
账房先生不懂。几百两白银,足够开一家小钱庄。为何要花在这些转瞬即逝的女人身上?
胡雪岩心里明镜似的,每一场婚礼,都是一次免费广告。
杭州城里有多少双眼睛盯着胡家的大门?
有多少张嘴在茶馆酒肆传播着最新的桃色新闻?
当人们惊讶于胡雪岩的风流时,更惊讶的是胡雪岩出手的阔绰。

三百两、五百两,说打发就打发,眼都不眨一下。
这样的人,钱庄能不稳吗?
1870年代,胡雪岩在《申报》上大做广告。钱庄还未正式营业,名声已经传遍上海滩。
商人们议论的不是胡雪岩的利率,而是胡雪岩的排场。
十三层楼的豪宅,成百上千的仆人,还有那些走马灯般更换的姨太太。
信用,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。
存款户把白花花的银子送进阜康钱庄时,心里踏实。
因为胡雪岩看起来太富了。富到可以随意挥霍女人,富到三百两银子如同三文钱。

这种"看起来的富有",比账本上的数字更有说服力。
账房先生后来才明白,那些遣散费不是开支,是投资。每一笔银两换来的,是市场对阜康钱庄的信心。
当商人们把几万两、几十万两的存款放进来时,那几百两的"演出成本"早已赚回千倍万倍。
胡雪岩甚至算过账。在《申报》刊登一次广告,要花几十两银子。娶一次妾,休一次妾,街头巷尾就会传上半个月。
哪种营销更划算?答案不言而喻。

杭州城的茶馆里,说书人添油加醋地讲着胡家的新故事。
听客们一边骂着胡雪岩薄情,一边感叹着胡雪岩的财力。
这种矛盾的情绪,恰恰是最好的宣传效果。
道德批判与财富崇拜,在晚清的商业社会里,从来都是一体两面。

空壳帝国的杠杆游戏
官府封条贴上胡府大门那天,所有人都以为会看到堆积如山的金银。
结果让人大跌眼镜。偌大的宅邸,华丽的陈设,账本上却只有可怜的几万两现银。
这个号称富可敌国的商人,原来是个精心包装的空壳子。

胡雪岩从来没打算真的"富",真正的秘密藏在钱庄的运作模式里。
存款户看到的是胡府的豪华排场,看到的是胡雪岩一掷千金的气派,于是心甘情愿把银子存进来。
这些存款转身就被胡雪岩用来放贷、投资、周转。
实际资本或许只有几十万两,撬动的却是上千万两的生意。
杠杆游戏的核心,在于让所有人相信你有钱。
胡府养着几百号仆人。每天的开销,光是吃喝就要几百两银子。

外人看来奢侈至极,胡雪岩算的却是另一笔账。
这些仆人本身就是活广告,走出胡府,个个西装革履、趾高气扬,杭州城里谁不知道在胡家当差是件体面事?
更精妙的是"人肉象棋"。
胡雪岩在自家花园里摆下棋局,真人充当棋子。身穿绸缎的仆人们按照指令移动,围观的宾客啧啧称奇。
这种匪夷所思的排场,成了商界传说。传说传得越远,阜康钱庄的信用就越值钱。
十三楼更是神来之笔,专门为姨太太们建造的楼阁,雕梁画栋,极尽奢华。

每一层住一位姨太太,杭州人戏称"杭州十三钗"。
这座楼的建造成本不菲,维护费用更是天文数字。值吗?当然值。
因为每个经过胡府的商人都会抬头看一眼那座楼,然后在心里盘算:能养得起十三个姨太太的人,钱庄还能不稳?
1870年代后期,胡雪岩的生意做到了巅峰。
北京、上海、杭州,到处都是阜康的分号。每一家分号的开张,都伴随着盛大的仪式,都伴随着胡雪岩的奢华亮相。
商人们排着队把银子送进来,根本不担心风险。

因为胡雪岩看起来太有钱了。
账房先生私下里算过真实的资产负债表。负债远远大于资产,现金流全靠不断吸收新的存款来维持。
这种模式有个专业名词,后世叫作"庞氏骗局"的雏形。
只要市场信心不崩,游戏就能永远玩下去。

胡雪岩深知这一点。所以每次娶妾、每次大摆筵席、每次豪掷千金,都是在给市场信心续命。
数百两的遣散费,几万两的楼阁建造费,在他眼里都是必要的"保险费"。
只要市场相信胡雪岩有钱,胡雪岩就真的有钱。

从"杭州十三钗"到12名离散的妾室
1883年某个深夜,胡府突然灯火通明。
管家挨个敲开姨太太们的房门,神色慌张。"老爷有令,每人领五百两银子,天亮前离开胡府。"
十三楼里传出哭声、质问声、摔东西的声音,这些曾经被精心供养的女人,一夜之间变成了需要清理的负资产。

只有正房太太留了下来,十二个姨太太,有的回了娘家,有的改嫁他人。
五百两银子,比当初娶进门时的聘礼还多。
胡雪岩做事向来大方,即便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,这份体面,是留给杭州城看的最后一场戏。
往前推十几年,"杭州十三钗"是整个江南最令人艳羡的存在。
每个姨太太都有独立的楼层,有专门的仆人伺候,穿的是苏州最好的绸缎,戴的是广东进口的珠宝。
胡雪岩偶尔兴起,会让她们一同出席宴会,十三个美人并排而坐,客人们看得眼花缭乱。

这种排场的成本惊人,账房先生算过,养活这十三个女人,一年要花掉几万两银子。
加上十三楼的维护费、仆人的工钱、各种节日的赏赐,开支更是无底洞。
普通商人早就叫苦不迭,胡雪岩却乐在其中。
因为这笔开销带来的回报,远超想象。
官员来拜访,看到"十三钗"的排场,自然知道胡雪岩的分量。
放贷的时候,利率可以谈得更低;借钱的时候,额度可以批得更高。
那些看不见的商业便利,都是这十三个女人换来的。
有时候,女人本身就是商品。

胡雪岩曾将心爱的姨太太送给某位封疆大吏。忍痛割爱的姿态,让那位大吏感念至今。
后来左宗棠西征,胡雪岩能拿到军需供应的大单,跟这种人情投资分不开。
女人在胡雪岩的商业帝国里,既是展示品,又是社交货币,还是风险对冲工具。
1880年代初,生丝生意开始走下坡路。
胡雪岩囤积的几百万两生丝卖不出去,资金链出现裂痕。
此时的"十三钗",从资产变成了负担。
每个月几千两的开销,在资金充裕时不算什么,在危机时刻却是压垮骆驼的稻草。

胡雪岩必须做出选择。
留下她们,意味着继续维持表面的繁华,但实际上已经没钱支撑这种繁华了。
遣散她们,意味着向市场承认:胡雪岩的好日子到头了。
两害相权取其轻,胡雪岩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——给足银子,体面地送走。
五百两不是小数目。对于普通人家来说,足够生活好几年。
胡雪岩用这笔钱,买下了最后的尊严。
杭州城里依然在传说,胡家虽然败了,老爷对女人还是大方的。

这种口碑,在胡雪岩看来,比什么都重要。
因为商业帝国可以倒塌,个人信用必须保住。只要信用还在,总有东山再起的可能。
可惜,留给胡雪岩的时间,已经不多了。

信心崩塌的72小时
1883年冬天,上海滩突然流传消息:阜康钱庄周转不灵。
谣言如同瘟疫,三天内传遍江南。
存款户们慌了,那些曾深信胡雪岩的商人,连夜涌到钱庄门口要求取款。
队伍从黎明排到黄昏,掌柜嗓子喊哑,说钱庄没问题,没人听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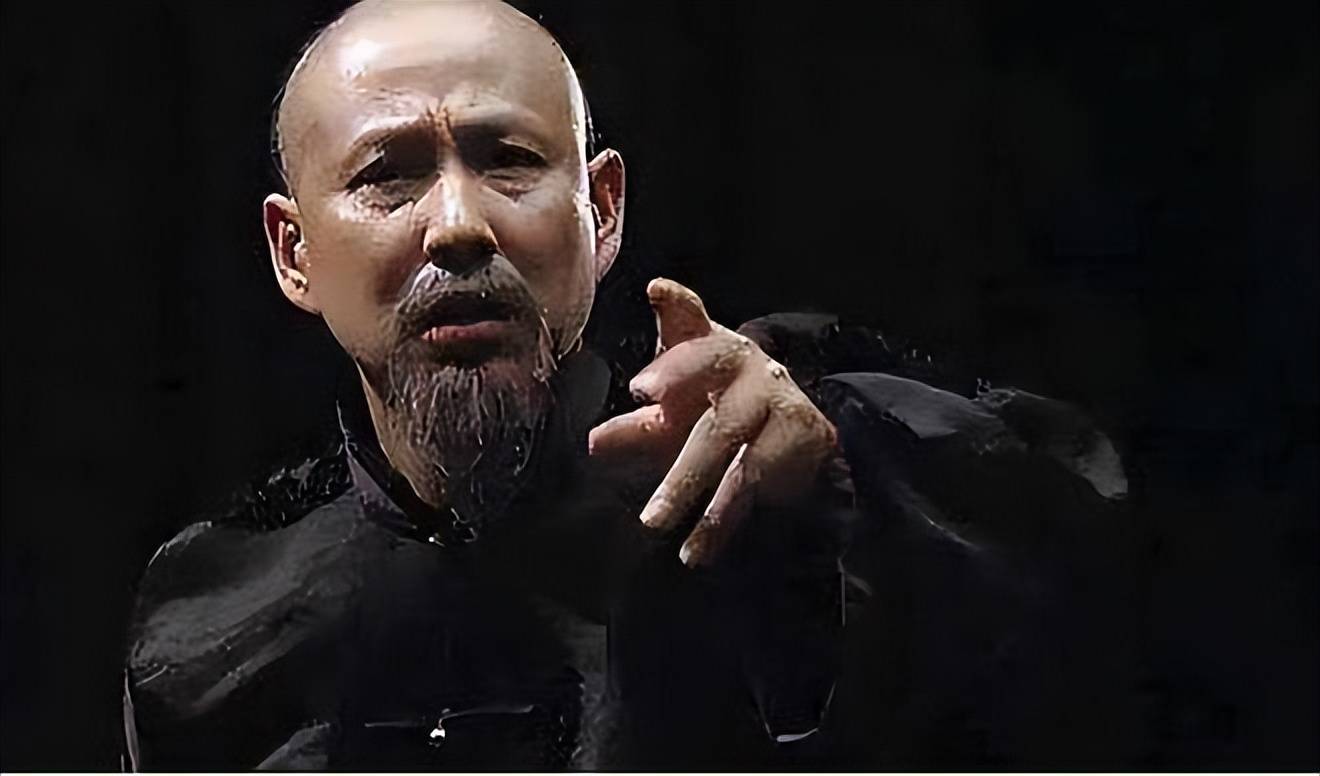
信心一崩,任何解释都没用。
李鸿章暗中推波助澜,早就看胡雪岩不顺眼的他,趁生丝生意失败,联合盛宣怀发动致命一击,在商界放风,说阜康资不抵债,还安排人带头挤兑。羊群效应立刻爆发。
72小时内,钱庄现金被抽空,胡雪岩四处筹钱,能借的都借遍了。
曾经毕恭毕敬的官员商人,如今纷纷避而不见,墙倒众人推,人脉在危机面前一文不值。
北京传来消息,欠款达一千两百万两,无力偿还。
那些曾用来制造“富有假象”的排场,此刻成了讽刺。

十三楼依旧华丽,“人肉象棋”早已散场。
《申报》的广告还在刊登,高利率却再也兑现不了。
数百两遣散费、几万两排场费、几十万两豪宅建造费,本想换来信心,如今全成废纸。
虚拟信用与实体资产错配,彻底暴露。
官府查封胡府时,在账本上看到骇人数字,资产不过几十万,负债却超千万。
那些精心包装的“富有形象”,原来是空中楼阁。

胡雪岩用几十万撬动千万生意的杠杆,在信心崩盘时反噬自身,将商业帝国压成齑粉。
1885年,胡雪岩郁郁而终。
没有翻身,没有反击。曾经风光的红顶商人,最后在破败小院里凄凉收场。
“杭州十三钗”早已散尽,十三楼逐渐荒废。
杭州城还在讲胡雪岩的故事:如何从学徒做到首富,如何一夜倾家荡产。
故事终归成了故事,教训成了教训。

晚清商界,信心最值钱,也最脆弱。
胡雪岩用一生证明:信心在,就是首富;信心崩,就是空壳。
那些几十万排场、数万接待、几百遣散买来的信心,经不起一次真正的考验。
账房先生最后在账本上写下一行字:演出结束,人去楼空。
参考信息:
《胡雪岩频繁娶妾,常常一夜过后就休掉,学者:难怪胡雪岩能成首富》·凤凰网·2020年
《胡雪岩娶了多少个妻妾?一夜破产,人都散尽,只有原配不离不弃》·文汇报·2019年12月6日
